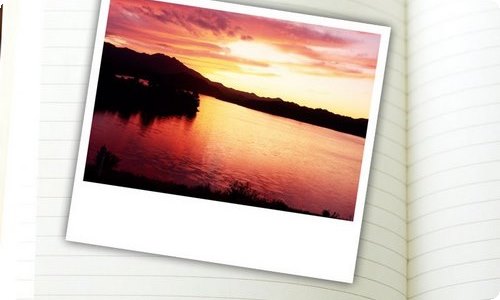《记忆》随笔

《记忆》随笔
在日常学习、工作生活中,大家对随笔应该都不陌生吧?随笔可以观景抒情,可以睹物谈看法,可以读书谈感想,可以一事一议。为了让大家在写随笔的时候更加简单方便,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《记忆》随笔,供大家参考借鉴,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。
《记忆》随笔1小满过后,老天落了一场很及时的小麦灌浆雨,田里的麦子是一天一个样,眼看就进入麦收季节了,大街上不时有大型收割机昂着头很威武的轰隆而过,休息了一年,它已聚足了能量,急不可耐的为即将到来的麦收战役而准备大显身手!因为有了它,现在的麦收才没有了当年的紧张、焦灼,三五天过去,遍野的金黄就剩下了齐刷刷的麦茬,曾经最为繁重的劳作就这样轻描淡写的结束了。提起麦收,人们不再当回事,我常常为此感到轻松、欣慰,但又有那么一点点遗憾、失落……
当年麦收可是北方农村一年里最繁忙、最热闹的日子,称为“火麦天气”,一切都为麦收让路,和老天爷争时间抢速度,只有把麦子全部收进粮仓,人们脸上才会露出舒心的笑容。 那些经典的最具夏收特色的标语口号“龙口夺食,分秒必争”,“抢收抢种,人人出动”,“细收细打,颗粒归仓”,“麦场重地,禁烟禁火”等等,几乎在每个村的墙壁上、麦场边都能看到。参加工作后,每年的麦收季节,厂里都会组织我们到工厂附近的村子里支援夏收,我们带上自备的磨得锋利的镰刀,奔赴麦田,参加这场大会战。一般三人一组,占九垄麦子,每人三垄,身手快、技术好的割麦能手担当中间“拱洞”重任,左手揽住三垄麦子,右手的镰刀沿着麦秸根部,均匀清脆的刷、刷、刷三声,三垄麦子变戏法般顺入怀中,随即将一揽麦子放在身体左后方,五六步放一堆,整齐有序,一路率先前行,拱开一个麦洞,相随的左右两人叫“挎翅”,紧跟上来,竞相追逐!大家比谁割的麦茬低,谁掉的麦穗少,开始还精力充沛干的热火朝天,互相打趣、说笑话,不时还吹吹牛,说他们是“慢三亩”,意思就是一天最慢都能割三亩麦子。不一会,一些吹牛者开始累的气喘吁吁,汗流浃背,耷拉着头也不说“慢三亩”了。也有一些割麦“把式”不太好的人,锋利的镰刀常常和皮肤亲密接触,不是胳膊上划了口子,就是腿上挨了一镰,但嘻嘻哈哈都不当回事。我们一些女同志、老同志做捆麦子的活计,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会了好几种捆麦子的方法,我特别喜欢使用一种“懒钥子”捆麦子,用这种方法捆麦子比平常的那种捆法速度要快,只是没有那种捆的麦个子式样美观,但为了速度,我们大都采用这种办法。麦收时节村里会开一段时间的食堂供群众吃饭,我们也就享受几天不掏饭票的美餐,下午的晌长,村里每天到黄昏时还给我们送一趟“贴晌饭”,大家吃的那叫一个香!这种记忆至今难忘!
八十年代初,家家都分了责任田,每年六月初小麦即陆续开镰,厂里会放几天假让工人回家收麦子,我们就到集市上买几把镰刀、几顶草帽,还会买一些白糖、橘子粉等防暑用品,赶回家和家人一起参加历时十来天的麦收攻坚战。每天早上天还蒙蒙亮的时候,就会听到院子里霍霍的磨镰声,我们便赶快起床,公公脚边已放了好几把磨得锋利的镰刀,它们放着幽幽的青光,在等着去施展身手。我们拿上镰刀和婆婆准备好的开水、馒头和黄瓜来到麦地里,已有不少人趁早上的凉爽开始干活了,一顶顶草帽在麦浪里交错起伏,挥舞的镰刀在宁静的田野上铿锵激越,让人萌生一种出征前的万丈豪情!我知道自己割麦不在行,便自告奋勇的去捆麦子,开始公公对我的那种“懒钥子”捆法很不以为然,把我捆好的麦子拿起来在地下摔打几次,看会不会散伙,试过后觉得还算结实,也就认可了这种捆法。其实捆麦子的活计一点都不轻松的,几天下来,胳膊上全是麦芒划的一道道红印子,汗水一渍,生疼生疼的,胳膊经过几天的暴晒,通红通红的还伴有灼烧感,几天之后会脱层皮,每年都是如此。
干到七八点钟,太阳已升的很高了,慢慢开始施展它的神威,我们浑身都是汗淋淋的,感到肚子也饿了,这时公公拿出婆婆给我们准备的食物,馍馍和黄瓜,坐在地头,一口馍馍一口黄瓜,觉得真是好吃极了,吃喝完毕,顿觉神清气爽,浑身来劲。多少年过去了,经常想起那个情景,却似乎再也没有吃过那样香甜的馍馍!
麦子割完后,还得一车车运回打麦场,有牲口的人家用胶皮轱辘车,一车能装将近一亩麦子,我们家没牲口,就用小平车拉,一亩地要拉好几车。一般是丈夫在前面拉,借助平车的背带,弯腰蹬腿使出全身力气往前行,公公在后面也是猫腰用力推,那真真是一滴汗水摔八瓣!运完麦子,丈夫的肩膀会被平车的背带勒出一道渗血的红印子,好多天才会消失。运回麦场后,为防变天下雨,得拿准备好的帐篷把麦垛子盖住,等待碾麦子,要是逢上连阴雨,长时间不能碾打,那麦子就会有些变质,蒸出来的馍馍有一种很难吃的霉味,所以每家都想用最快速度把麦子碾完,把麦颗收回家,悬着的心才会踏实。最初几年是用牲口拉石碌碡碾麦子,这是一道繁重冗长的工序,碾场这天,要提早把麦个子散开均匀的摊在打麦场,让太阳晒一会,碾的中间还要用木杈翻几次场,往往需要几天时间才能把麦子碾好,家里人手少的还得叫上主要亲戚来帮忙碾场。我们家没牲口,得等别人家的牲口闲下来才能借用,已出嫁的两个妹妹和妹夫也都赶过来帮忙。
碾完后还得“扬场”,就是把糠秕从麦颗中分离开,这不仅是个力气活,更是个技术活,需要借助风力用木掀一掀一掀撮起上扬,还要固定在一个落点,下面有人专门用扫帚捋去麦粒上的麦糠和碎屑。扬场者那一招一式,就像一个舞姿优美的舞者,每次扬起来的麦子,宛如划过一道彩虹,令人赏心悦目,一家几千斤的麦子,就这样一掀掀扬了出来。后来有的家置办了扇车,就互相借着使用,不再费力气扬场了。再后来有了大型脱粒机,更是减轻了人们的劳动强度,效率也大大提高,像我们家七八亩麦子,几个小时就好了,而且脱出来的麦粒干干净净,不需再扬场了。一般是几家合伙使用一台脱粒机,轮到脱粒这几天,几家人老少齐上阵,白天黑夜连轴干,累了就在麦垛旁边打个盹。麦场上,机器轰鸣,人声鼎沸,有一个公认的主事人,像个战场上的指挥员,指挥大家各司其职,年轻力壮的,负责将麦子均匀的喂入高速运转的脱粒机内,有几个人专门往脱粒机前转送麦个,并将捆麦子的“钥子”解开,脱粒出来的麦秸秆要旋成一个很结实的圆形的麦秸垛,这也是个技术活,一般人拿不下来,都是由经验丰富的庄稼把式完成这个杰作。有人在机器出口把脱粒出来的麦颗装进口袋。机器不停的轰隆隆响着,说话需要很大声别人才能听得见,每个人的脸上都落满了麦秸秆的碎屑,鼻孔和耳朵眼几乎都堵塞了,眉毛和眼睫毛也成了灰白色。虽然很累,但大伙兴致都不减,很大声的说着笑着。有邻家大哥很有才,四六句张口就来,大家都很喜欢听他说,每次听到他流畅的顺口溜,就让人联想到赵树理笔下的李有才。不时有人喊,来一段,解解乏!邻家大哥一句“好咧”,“张家媳妇李家婆,故事能有几大箩……”幽默诙谐的段子不假思索的就从那满是灰尘的嘴边流淌出来,大家开怀的笑声淹没在轰隆隆的机声里,疲惫也似乎飞到了九霄云外。
不久,麦地里出现一种简易收割机,是安装 ……此处隐藏19576个字……,用一个“笊篱”把米饭捞出来,米饭就被放进这个“浅子”里,锅里有一个用木头制作的架子,架子下面放一点水,装满米饭的“浅子”放在架子上面,把水烧开,一顿香喷喷的米饭就做出来了。
我始终没有见过奶奶或者其他人是如何制作“浅子”的。但从形状、秸秆疏密相间的要求来看,其制作工艺的技巧,要求应该是相当高的,可以说是高粱秸秆编制技巧之集大成者,代表了秸秆制作最高技艺,集中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。
高粱秸秆制作的生活用具,不知始于何时何处,不知是那位能工巧匠的专利,也许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活中的集体智慧的结晶。现在,虽然很少见到那些用具了,但并没有绝迹,在城乡人家的厨房,也会间或看见它们的踪影,时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。我家里如今就有几张这样的锅盖,不是用来盖什么,是在包饺子的时候放饺子用的。包好的饺子放在上面,顺着秸秆的脉络摆放,不漆皮、不粘连,横竖成行,美观、环保。
但是,随着社会的发展,那些曾经在家庭里常常使用过的用具,难免随岁月的流失,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,成为记忆的一部分。或许,随着一代一代人的消失,最终也会被历史的尘埃封存,也会记忆不在,成为故事里的一部分。
二、摁倒了葫芦起了瓢
这是说葫芦的,也是说瓢。葫芦是一种植物,瓢则是一种日常生活用具。
记得小时候,家里房前屋后,总会搭起很多架子。葫芦的藤蔓就沿着搭好的架子攀爬,到了盛夏季节,藤蔓爬满了架子,纵横交错。翠绿的叶子从藤蔓生出来,覆盖在架子上面,遮住了空中炎热的阳光,洒下一地浓荫,一地斑驳的光影。这个时候,人们就会在那爬满葫芦藤蔓的架子下面,摆放一张圆桌,几把椅子,沏上一壶茶,让袅袅茶香氤氲一院。家人或者三五好友,围坐在阴凉处,纳凉、品茶、谈天说地,享受一段美好时光。
盛夏过后,那些招摇的花儿谢了,一个一个小铃铛一样的葫芦,从花蒂出结出来,嫩嫩的,新鲜可爱。此时,正是光照充足,雨水丰沛的时候,那些刚刚结出的小葫芦,就像吹了气的球,眼瞅着往大里长。我们这些孩子们,就会站在葫芦架下面,手指着一个个的葫芦,大声数着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数着数着,一阵风来,那些叶片被风吹翻,不知又从什么地方露出几个葫芦,在风中摇晃。孩子们乱了,再也数不清楚,嚷嚷一阵,向院外跑去。
转眼之间,天气转凉了。葫芦架上那些又大又绿的叶片,渐渐发黄、枯萎、衰败。那些吊在藤蔓上的葫芦,不再往大里长,有的颜色开始变化,翠绿渐渐变成黄色,用手指轻轻弹击,发出一种悦耳的声音,这说明,葫芦已经成熟了。
年景好的时候,一架藤蔓会结出很多葫芦,从架子上悬挂下来,大大小小,长长短短,形状各异,在风中摇来晃去,一幅很美的景致。葫芦的大体形状差别不是很大,但细微之处,就有不小的区别。有的长得很圆、很大,由一根细细的藤蔓牵引着,只有藤蔓处是细细的,然后,迅速膨胀,像极了充足了气的气球。这是人们比较喜欢的形状,不是因为形状美观,是因为这样形状的葫芦,符合人们使用的要求。成熟,晾晒之后,用刀从中间剖开,就是极好的瓢。更多的则是中间极细,两头圆圆的葫芦,很具观赏价值,这样的葫芦,从葫芦的顶部切开一个小口,可以用来灌水、盛酒、有的还用来装那些小药丸。
葫芦成熟以后,被秋风一吹,色彩就慢慢发生变化,由青绿渐渐向青白、青黄转变。这是岁月留给葫芦的礼物,也是葫芦成熟的象征。这时候的葫芦是最为美妙的了,仔细观察,那些葫芦的颜色几乎每天都在变化着,而且变化的过程只可以感觉得到,却无法看见。昨天这个地方还是青绿的,转眼之间,绿色淡去了,更多的白浮上来,或者一团一团的金黄晕染出来。那种自然天成的色泽,那样浑然一体的变化,比那精致的青花瓷不知美妙多少倍。那就是天然的艺术品,是大自然的杰作,是任何能工巧匠都无法企及的顶峰。
那个时候,家里几乎见不到铁制或者塑料的用来舀水的水舀子。家家户户使用的大都是这种用葫芦制作的水瓢。这样的用具不知是谁发明的,世世代代使用于民间。从材料记载看来,葫芦的使用,在我国已经有很长一段的历史了。在中国河南考古遗址出土的葫芦皮最早的是七至八千年前的,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葫芦子也有七千年的历史了,有些学者怀疑在甲骨文中就已经有葫芦的字了(卣)。中国最早将葫芦称为瓠、匏和壶。在《诗经》、《论语》中均有葫芦被提到。一个例子是《诗经.豳风.七月》中的“七月食瓜,八月断壶”。
按照《白虎通》的记载,笙本来是葫芦做的(瓠曰笙)。唐朝刘恂也写过:“交趾人多取无柄老瓠,割而为笙,上安十三簧,吹之,音韵清响,雅合律吕。”《尧典》有“金石丝竹匏土革木”。直至今天在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中,依然有用葫芦制作的乐器使用,如葫芦丝。
道教认为葫芦可以凝聚气,因此使用葫芦装丹。在道教中葫芦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容器,而有法器的作用。
在漫长的种植与使用过程中,我国古代劳动人民,不但将这种自然植物运用于生活之中,还赋予种种浪漫色彩,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美丽传说,让葫芦充满了传奇色彩。
农村种植葫芦,自然不是为了满足浪漫的想象,也很少用来盛水、装酒,更多的是用来制作一种用来舀水的用具,俗称“水葫芦”。前几年回老家,还看见不少人家的水缸里,还使用这种用葫芦制作的瓢。熟透了的葫芦外表呈金黄色,质地坚硬,有一种金属的质感,而且轻巧而坚韧。长期浸泡在水中,不腐烂、不褪色、不变形,更妙的是轻飘飘的,却是十分坚挺,无论多大的水瓢,都可以舀满满一瓢水,不颤、不抖,不会将水溢出来。用完之后,随手放在水缸里,水瓢就在水面漂着,永远不会沉到缸底。
用葫芦制作的水瓢,同样具有经久耐用,经济环保的特点,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。是的,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的先人,用葫芦制作成舀水的水瓢,简直就是完美的创造。大自然中,自然界的植物可谓千千万万,数不胜数,可是细细想来,有哪一种植物,可以替代葫芦的用途呢?
葫芦,在千百年的里程中,由植物演变为用具,演变为艺术品。是葫芦的造化,也是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体现。
那些离我们越来越远的生活用具,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,一种生活的变化,也蕴含着我国劳动人民认识自然,改造自然,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美好心愿呢。
《记忆》随笔15窗外是纤尘不染的天空,搁浅的流云,几只黑燕停在电线杆上,也不吵闹,静静的,像极了画框里的水彩。时钟也不慌乱,连空气都带了几分闲散。
我忘了这是第几次坐在窗前发呆,看手表上的分针一圈一圈不厌其烦地走,夕阳染黄了墙,似火的霞竟也是没有温度。
来来往往的行人,急匆匆的脚步,我终耐不住寂寞走在街道上,渐起了风,路灯也一盏一盏的亮起。透过橱窗,看里面的商品琳琅,灯光拉长了身影,很长,直通向那边的黑暗。暖黄的灯光映着不算太暗的夜色,织起的黑锦平铺着,我抬头,任凭天空落下些许寒冷的碎屑在我脸上。
少年模样已老的心,都忘了是谁对我的评价,现在想想好像确实如此。我想一个人去旅游,背个背包,带着满脑子的回忆,去自己想去的地方,做个关于自己 梦。静静 地就这么陪记忆老去,成为陈迹,再厚的笔记本想必也记不完这些琐碎的记忆,沧海里,一个故事就是一粟。

文档为doc格式
- 1【精】童年趣事优秀作文
- 2关于自立自强的演讲稿4篇
- 3学校师徒结对发言稿
- 42022年教师读书活动总结
- 5岗位求职自荐信
- 6悲伤意境的个性签名
- 7实用的班级年工作计划汇编五篇
- 8工作唯美语录句子大全(通用80句)
- 9酒店前台工作总结范文
- 10精选学生学习计划模板汇总9篇
- 11愿你开头的唯美句子
- 12关于正能量格言语句30句精选
- 13辞职报告
- 14工作方案
- 15活动总结
- 16主持稿
- 17实习报告
- 18学习总结